掣鯨:杜詩的兼容與沉厚
編者按:近日,歐麗娟《竹影鯨歌:杜甫的意象世界》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一千多年以來,杜甫的“詩圣”的地位可謂無人可堪比肩,作為詩國中光芒萬丈的集大成與開新者,杜甫之詩風(fēng)格渾成,意象獨(dú)出。歐麗娟致力于足以顯發(fā)杜甫生命與藝術(shù)成就的標(biāo)志性意象,吸收傳統(tǒng)中的灼然慧見,將杜詩意象納入《詩經(jīng)》以來的整個(gè)詩史發(fā)展脈絡(luò)中觀察,更借鑒西方文學(xué)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觀察分析的眼光,由此可以具體而微地理解杜甫何以為詩圣。經(jīng)出版方授權(quán),中國作家網(wǎng)特遴選其中《大鯨意象》一節(jié)發(fā)布,以饗讀者。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注釋請參見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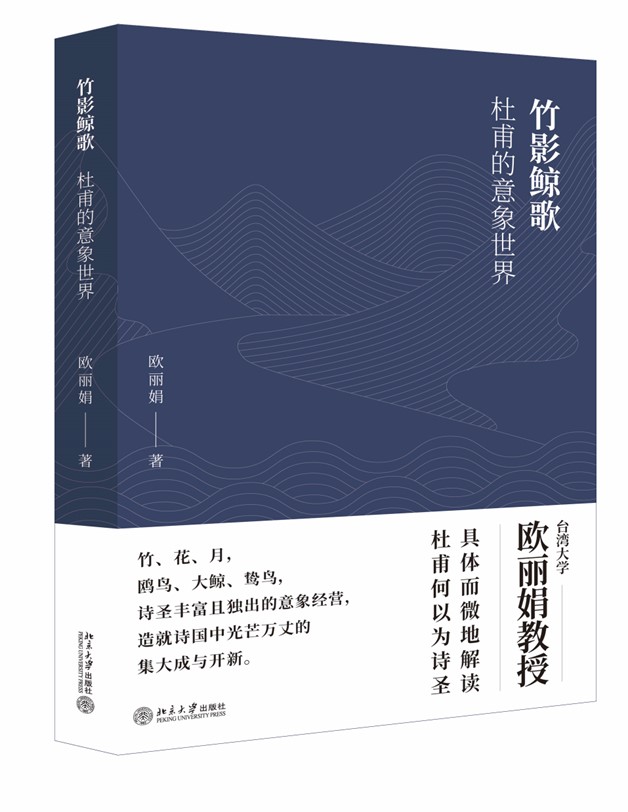
《竹影鯨歌:杜甫的意象世界》,歐麗娟 著,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4月
“鯨”之意象在文學(xué)史中并不是詩人文學(xué)家經(jīng)常處理的題材,但在杜甫集中卻一共出現(xiàn)有十六次之多,超過六朝同類數(shù)目之總和;且這十六首蘊(yùn)含鯨之意象的詩作,在時(shí)間涵蓋面中綿延了詩人一生,其間并不斷持續(xù)出現(xiàn),少有中斷,不但是透露詩人精神志氣之憑借,尢其重要的是我們據(jù)以了解杜甫詩論的一條線索。因此,本節(jié)要就歷代鯨之意象運(yùn)用,及杜甫詩作的運(yùn)用內(nèi)涵來進(jìn)行探討。
《莊子·逍遙游》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崔譔、簡文之訓(xùn)解并云鯤當(dāng)為鯨。若此,則文學(xué)史中最早出現(xiàn)鯨之意象者,此處即為其一;唯郭慶藩已辯其非,謂鯤乃大魚之名,與鯨無關(guān),崔譔、簡文之說皆失之,因此,我們在探討杜詩中鯨之意象之前,必須另尋源流,以作為比較之基礎(chǔ)。
《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yù)注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此處的鯨是一種純?nèi)回?fù)面的象征,其不義之喻也塑造了鯨意象表達(dá)上內(nèi)涵的一個(gè)側(cè)面,不但漢朝李陵《答蘇武書》所言“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并為鯨鯢”。直接繼承此一典故,以鯨吞喻無辜妻子為不義所害,并且直接影響到杜甫對鯨之意象的運(yùn)用角度,成為杜詩中鯨之意象的主要源頭之一。降至(東漢)六朝,賦體文學(xué)大興,投入此種“體物而瀏亮”。之文體的創(chuàng)作者頗有其人,作品中涉及鯨魚者更機(jī)率大增,如張衡《西京賦》的“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左思《吳都賦》的“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和“鰴鯨背中于群犗,攙搶暴出而相屬”,而木華(字玄虛)所作的《海賦》更對鯨魚氣魄之浩大、聲勢之駭人有著極夸張而生動(dòng)的描繪:
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游,戞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云,鬐鬣刺天,顱骨成岳,流膏為淵。
這樣的鯨不但沒有絲毫不義之意,反而以其橫海吞舟、插云刺天的突兀氣勢,被藉以為形容京都或大海之雄偉磅礡的襯托,其勢愈壯觀,京都大海之氣魄在烘托比較下也愈驚人。這種極力體物、夸筆描摹的方式使“氣勢的展示”成為賦體中鯨之意象的主要內(nèi)容,構(gòu)成了杜詩中同一意象運(yùn)用的另一重要源頭,可作為了解杜詩意象的參考背景。
六朝除賦體外,詩歌體中也出現(xiàn)過鯨魚的意象,在這些極少數(shù)的例子中,陶淵明《命子詩》繼承了“不義之鯨”的用法,曰:“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繞云,奔鯨駭流。”感嘆不義橫行、正人幽隱,意象鮮明,謝脁《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詩》之“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更以之類喻五胡亂華;另外,于梁簡文帝《詠煙》的“欲持翡翠色,時(shí)吐鯨魚燈”和陳江總《雜曲三首》之三的“鯨燈落花殊未盡,虬水銀箭莫相催”中,鯨則以燈的造型出現(xiàn),只是一般的形象而無人文上的象喻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外,用到鯨魚意象者絕大多數(shù)為石鯨,如梁朝劉孝威《奉和六月壬午應(yīng)令詩》的“筑山圖碣岫,穿池控海潮。雷奔石鯨動(dòng),水闊牽牛遙”、隋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詩》的“池鯨隱舊石,岸菊聚新金”、虞世基《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詩》的“支機(jī)就鯨石,拂鏡取池灰”和任希古《昆明池應(yīng)制》詩的“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等皆是,入詩之石鯨都取資于晉葛洪《西京雜記》所述漢武帝鑿昆明池刻石為鯨的故事 故事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dòng),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yàn)。”又《西都賦》注:“武帝鑿昆明池,于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是為石鯨意象之所本,但直襲其意,寓目則書,語意新巧,卻深思不足;此外,南朝為數(shù)眾多的詠物詩中也難得地出現(xiàn)一首詠鯨詩,這唯一一首是陳代周弘正的《詠石鯨應(yīng)詔詩》:
石鯨何壯麗,獨(dú)在天池陰。騫鰭類橫海,半出似浮深。
吞航本無日,吐浪亦難尋。圣帝游靈沼,能懷躍藻心。
此詩以鯨無奈為石質(zhì)的悲心出發(fā),從舊典中翻出新意,將石鯨徒有壯麗外觀,卻吞航無日、吐浪難尋,連浮水潛深之本能亦被剝奪的悲哀表達(dá)得極為感人,其“類”字“似”字含有多少似真而實(shí)幻的失望之意,可以說是一首深帶移情作用的詠鯨佳作。值得注意的是,各詩吟詠的多是鯨燈、石鯨等人造物,與賦體所鋪排夸揚(yáng)的海鯨各屬兩類,追究其故,應(yīng)是不同體裁各有不同聞見焦點(diǎn)的自然限制使然;而綜合兩類觀之,除少數(shù)詩例如周弘正《詠石鯨應(yīng)詔詩》外,大多是出于一種站在物象距離之外的客觀描述態(tài)度所塑造,因而較不能引發(fā)飽滿的象喻意味。原本詩歌創(chuàng)作的美感經(jīng)驗(yàn)里,心物之間也須維持一“心理的的距離”(psychical distance),以使物我關(guān)系能超脫現(xiàn)實(shí)的利害計(jì)較,而能產(chǎn)生美感欣賞的觀照;然若在此一“心理的距離”形成時(shí),主觀情感的投入?yún)s又不足以融入對象之中,使之經(jīng)由心靈綜合作用而化為飽和的意象,則此物象仍只是一客觀外物而已,并不能打動(dòng)人心;以上所論鯨魚意象表現(xiàn)不足的地方,可以說就是“有適當(dāng)距離而無深厚感情”。
另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六朝詩中運(yùn)用的鯨魚意象總數(shù)并不多,個(gè)別看來,又為各家集中孤例,顯然此一意象并未受到詩人的充分注意。到了杜甫手中,不但綜合了上文所言種種不同的對象(石鯨、海鯨)和意涵(不義之喻、雄偉之氣勢),且后出轉(zhuǎn)精,為鯨之意象充實(shí)了更豐富的層次和內(nèi)容,足以作為探尋詩人多方意向的根據(jù)。杜集中與鯨之意象有關(guān)的十六首詩作,前后間含義互見、喻意雜出,為便于掌握起見,茲依其內(nèi)容指涉歸為三類來進(jìn)行討論。
第一類是屬于南朝鯨之意象主流的石鯨意象,出現(xiàn)于杜詩中只有一處;但雖僅有一例,卻對石鯨意象之塑造有極為超越的成就。夔州時(shí)所作《秋興八首》之七云:
昆明池水漢時(shí)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jī)絲虛夜月,石鯨麟甲動(dòng)秋風(fēng)。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guān)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心眼中仿佛可見的漢武旌旗盛功浩偉之景,于詩人的深沉觀照中,逐漸抽離現(xiàn)實(shí)之輪廓,終而泯滅今昔,化出一片荒涼凄清之虛象,在秋風(fēng)夜月和漂、沉、墜、冷、黑、紅、虛等字質(zhì)交織作用而成的寥落荒蔓中,自生隱隱欲出的動(dòng)蕩危疑之感;尤其沉沉黑夜里似有危機(jī)四伏,連亙古不移之石鯨也為秋風(fēng)所撼動(dòng)而鱗甲欲掀,此一幻覺正足以顯發(fā)觀照者強(qiáng)烈不安的心緒。葉嘉瑩先生說:“織女句自有一片搖蕩凄涼機(jī)絲徒具之悲,石鯨句自有一片搖蕩不安鱗甲欲動(dòng)之感,非唯狀昆明之景生動(dòng)真切,更復(fù)有無限傷時(shí)念亂之感,而于政之無望,時(shí)之不靖,種種感慨,皆借此意象傳出,寫實(shí)而超乎現(xiàn)實(shí)之外。”又說:“以意象渲染出一種境界,于是織女石鯨乃不復(fù)為實(shí)物,而化成為一種感情之意象了。”這種不為現(xiàn)實(shí)所拘限的表達(dá),較之六朝石鯨意象,不但使石鯨復(fù)活而生動(dòng)逼真,深深徹入一股內(nèi)在心靈與情感強(qiáng)大力量,而且內(nèi)容上溝通今昔,意旨更為豐實(shí)凝煉、涵厚沉郁,遠(yuǎn)非前此者所能比擬,在詩歌傳統(tǒng)中,正是一種高度之超越與開拓。
第二類是比喻天寶年間顛覆大唐江山幾近亡國的安史之亂造反叛變的意象,詩中出現(xiàn)者凡四處:
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島。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晦日尋崔戢李封》)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遺孽尚縱橫。(《奉送郭中丞充隴右節(jié)度使》)
妖氛擁白馬,元帥待琱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觀兵》)
公時(shí)呵貐,首唱卻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睢。(《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安史之亂首尾凡八年(玄宗天寶十四年至代宗廣德元年),初起不久,半壁天下便望風(fēng)瓦解,京師震動(dòng),不但玄宗棄京入蜀,太子北行;亂平后大唐國勢也即頹敗不起,殷憂踵繼,命脈衰危。杜甫詩中以鯨比之,所謂鯨吞九州島,地翻而百川亂流之描述,將攸關(guān)國運(yùn)的歷史事實(shí)化為詩歌意象,不但極具凝縮之效,使歷史事件之復(fù)雜得到概括性的點(diǎn)明,其象喻效果也使之脫去說理性質(zhì),而具有詩歌藝術(shù)的感人力量,因此此類鯨之意象比較其《左傳》和李陵書的源頭,和陶淵明“奔鯨駭流”之描述,更加深了氣勢表達(dá)的聳動(dòng)性和對其不義之深重的感受;再則“斬鯨”“卻鯨”之詞也在鯨本已浩大之氣勢上翻上一層,突顯了杜甫一意斬除不義的磅礡壯心,氣勢之上再增氣勢,手筆之大前人莫比。這是鯨結(jié)合不義之意最生動(dòng)的表現(xiàn)。
第三類是杜甫鯨之意象表現(xiàn)最主要的內(nèi)涵,充分展現(xiàn)了詩人的生命意向與創(chuàng)作理想,就后者而言,尤其是杜詩中豐富的意象群里最值得探究的主題之一。先就展現(xiàn)詩人的生命意向而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有極完整的表達(dá):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zhuǎn)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dú)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詩作于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變前夕,全詩“不僅將沿途所歷與自己客居長安十年來之感遇作一總檢討……同時(shí)也寫出杜甫內(nèi)心對君國去就之矛盾”。在去就矛盾中,顯然杜甫是深恥如螻蟻般自求其穴的干謁之輩,而選擇現(xiàn)實(shí)上兀兀為塵埃所沒,操守上卻不逆己志的理想,這個(gè)遙比稷、契以天下百姓為襟懷的生命,有著最寬大厚實(shí)一如溟渤的內(nèi)涵,只有大鯨才能涵攝包容進(jìn)去;所謂“以茲悟生理”即是詩人了悟、肯定這個(gè)超脫世俗自利、以天下為懷的道路,也就是由鯨偃溟渤之意象所體現(xiàn)的志向。這個(gè)志向在長安時(shí)期雖然已抑郁不償,卻仍不失壯厲之意氣。
但經(jīng)歷數(shù)年漂泊天地之磨折后,雖憂國懷民之心不減反深,然以登要路津來完成志業(yè)的從政方式卻已不為詩人想望了。廣德二年流寓成都時(shí)所作的《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中的鯨,便透露此一訊息: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fēng)濤涌,中有掉尾鯨。……
領(lǐng)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
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愧客茹藜羹。
這匹織鯨的貴重褥段帶給幽居草堂的杜甫一陣不平靜。掉尾于洶涌風(fēng)濤中的鯨氣勢驚人,其所在的錦段織成更是貴重,對于田舍短褐的詩人而言似乎是十分不稱的,其后遂以“服飾定尊卑”的理由卷錦還客,以免逾越等分而招致不祥之禍,并藉以諷喻嚴(yán)武鎮(zhèn)蜀奢侈之作為。然而從“始覺心和平”和“愧客茹藜羹”之語,也隱隱反映出杜甫“還鯨”之舉帶有安于閑野現(xiàn)狀,不汲汲于政治實(shí)踐的象喻意味,而長安時(shí)期的鯨所代表的積極進(jìn)取,至此成都草堂時(shí)期似乎已退由輕鷗之閑淡自安所取代(此點(diǎn)可參前一節(jié)之論析),消長之跡十分明顯。降及大歷三年,杜甫再度放棄夔州安定歲月,開始出峽萍居江湖,鯨之意象又有不同轉(zhuǎn)變。詩有三首,其一為《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詩云: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fù)江湖。……
溟漲鯨波動(dòng),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王嗣奭曰:“因雁影而問南征,因鯨波而想東逝,時(shí)尚未定所往,正應(yīng)起句。”浦起龍也說:“‘溟漲’四句,引到所往之處。本只之公安也,而曰隨雁‘南征’,復(fù)想騎鯨‘東逝’,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正上文‘萬國盡窮途’意也。”五十七歲的杜甫,日薄西山又前程茫然,躊躇于南征或東逝之抉擇,這時(shí)所見之鯨波非但已無壯心大志之寓托,亦復(fù)無閑居和平之安然,反而以其溟漲之勢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舟楫所在之江湖的廣漫無向,并反襯雁影之孤渺,與其欲投無處的徘徊之感。另外在《別張十三建封》詩中曰:“范云堪結(jié)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鯨魚。”以潮落鯨回比喻張建封之北歸,頗有寥落之意;又《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詩云:“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指出自己雖有志于到南海丹砂一償乘鯨之志,但身勞不耐跋涉,終于“不能乘鰲驂鸞,但作鳴鶴以吐意耳”,著一“聊”字更顯出杜甫無奈、退讓之心緒。總合起來,與前面兩個(gè)階段合并觀之,杜甫在鯨之意象中所透顯的是自己從經(jīng)世濟(jì)民的現(xiàn)實(shí)政治冀求上逐步飄離的生命軌跡,由長安時(shí)期慕大鯨、偃溟渤的壯懷厲氣、猛志橫逸,到成都時(shí)期卷鯨還客而心覺和平,再到出夔入峽為溟漲鯨波所惑以及乘鯨之志不遂,所謂“憂世心力弱”(《西閣曝日》)的最后階段,杜甫憂世傷民之心仍深仍切,但已漸從政治實(shí)踐之意圖退縮,配合前后對溟渤、溟漲等盛大水勢之不同態(tài)度,都足以勾畫其面對世界的意向轉(zhuǎn)變,若再結(jié)合前一節(jié)所論?dān)t鳥意象的表現(xiàn),此跡當(dāng)更為顯著。
另外,杜甫又以鯨之意象來體現(xiàn)對特定才性之雄大表現(xiàn)的感受,如其稱摹李適之豪量縱飲之容態(tài)為“長鯨吸百川”:
左相日興費(fèi)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圣稱避賢。(《飲中八仙歌》)
又贊嘆張垍、王直之才力雄大有如鯨破滄溟: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云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jīng)。(《贈(zèng)翰林張四學(xué)士垍》)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fēng)白日動(dòng),鯨魚跋浪滄溟開。(《短歌行贈(zèng)王郎司直》)
浦起龍注第一首詩曰:“一言官高而親,二言才雄而顯。”對照下面“紫誥”一聯(lián),可知其才在于“優(yōu)文翰也”,正合于《舊唐書》所稱“均、垍俱能文”。之說,二人才力磊落噴薄,足以沖出滄溟一詞所指謂的高杳廣漠之籠罩,尤其第二首在最前面兩句二十二字一氣不歇地縱貫推激之下,鯨魚跋浪之氣勢更如破竹般獲得加強(qiáng),其才力之雄厚也更加鮮明可感。
就才性展現(xiàn)于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鯨”也是我們了解杜甫詩觀的一條線索。他認(rèn)為詩的內(nèi)容要豐富,方法要兼綜博采,如鯨吸百川、納萬物一般;詩又要作得氣勢雄渾,才力迫人,有鯨吞波摧舟之勢;以下兩首詩就是這種詩觀之形象表達(dá):
才力應(yīng)難跨數(shù)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戲?yàn)榱^句》之四)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八哀詩·贈(zèng)秘書監(jiān)江夏李公邕》)
前一首借四種物象來提出有關(guān)創(chuàng)作態(tài)度或方法的意見,錢謙益注云:“‘凡今誰是出群雄’,公所以自命也。蘭苕翡翠,指當(dāng)時(shí)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匯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正指出杜甫以掣鯨之意象傳達(dá)一種兼容并包、廣納萬川的創(chuàng)作觀點(diǎn)。碧海浩瀚無垠,羅藏?zé)o數(shù),能掩其溟漠,縱游不羈者,唯鯨足以當(dāng)之;而當(dāng)其縱適于煙波浩蕩中時(shí),氣勢是噴薄雄大的,后一首楊倫引趙注曰:“鐘律比聲之和雅,鯤鯨比勢之雄壯。”可見除了廣納博涉之外,氣勢雄偉也是杜甫詩觀重要的一面。于此更當(dāng)說明的是,唯其廣納萬川,不擇細(xì)流,故亦不排拒研揣聲律之作法,此觀“或看翡翠蘭苕上”的“或看”二字可證;而在其能博能精的才力胸懷下,不但不排拒聲律,甚且努力發(fā)揚(yáng),一方面將“詩之嚴(yán)者”的律體在個(gè)人創(chuàng)作中發(fā)揮到成熟的巔峰,一方面也是贊賞他人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此視“鐘律儼高懸”之稱許可知。這種廣而能深細(xì)、大而能不遺,在廣吸博納的同時(shí)亦無礙于詩律精密,在格律拘限中仍能噴薄縱橫的表現(xiàn),正是所謂“兼人人所長”的真切內(nèi)容。此一雄渾、廣包的詩觀在杜甫其他詩中也有明白的呼應(yīng),如:
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西閣二首》之二)
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dòng)搖。(《奉贈(zèng)盧五丈參謀琚》)
第一首詩中海的溟闊被比為人的思力詩才,第二首指出為窮盡人間豐富多樣的興味,就須縱身入海、窮盡思力搜求始能得之,這是杜甫明示作詩方法務(wù)須兼博的這一面而言。胡震亨曾指出:“非深于搜索者,無此想頭。李克恭《吊孟郊詩》‘海底也應(yīng)搜得盡’正祖此意。”另外張戒《歲寒堂詩話》對這種深于搜求之方法更有很具體的說明: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這種搜羅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的作詩法度,也直接決定內(nèi)容的博大富贍和思力的雄渾峻健,表現(xiàn)出來的詩歌效果也就如海凌絕島,力足以動(dòng)搖湖山,這正與“鯤鯨噴迢遞”之意象感受煥然相符;其他如“毫發(fā)無遺憾,波瀾?yīng)毨铣伞保ā毒促?zèng)鄭諫議十韻》)、“意愜關(guān)飛動(dòng),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賦詩賓客間,揮灑動(dòng)八垠”(《寄薛三郎中璩》)等,也莫不可由鯨之意象來加以貫連體現(xiàn),因此,王安石說:“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便是以掣鯨意象來總括杜甫詩歌的整體風(fēng)格。較之盛唐另一大家李白詩中的鯨,如“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其意味仍屬飄灑飛揚(yáng)之感,與杜作的沉厚雄渾大不相同,因此可以說,“鯨”是杜甫用以體現(xiàn)這種方法上兼綜博采、氣勢上雄渾偉壯兩方面之詩觀,且足以總括其創(chuàng)作之自許與實(shí)踐后產(chǎn)生之整體風(fēng)格的最主要意象。
總結(jié)本節(jié),可以發(fā)現(xiàn)杜甫詩中的“鯨”在一貫中有著復(fù)雜而豐富的內(nèi)容。一貫的是對“才雄勢大”之一種大生命的充分體現(xiàn),復(fù)雜豐富的則是在境界的提升,和層面或角度的擴(kuò)大。境界的提升如石鯨、不義之喻所表現(xiàn)者,層面或角度的擴(kuò)大如個(gè)人生命意向與創(chuàng)作觀點(diǎn)之投射,比較六朝詩中的鯨魚形象,杜甫經(jīng)營之刻意與寄意之深微十分明顯,因而也對傳統(tǒng)做了更大的突破和開拓,這也足以為肯定杜甫在意象發(fā)展史上之高度地位的一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