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索《持敬集》序:以崇敬之心,行守正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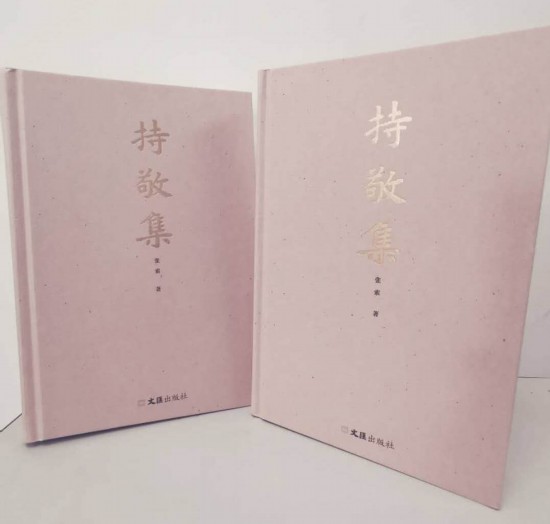
張索君將多年所寫的文章,編為一集,首先讓我讀過,希望我能談談看法。一頁頁翻閱過去,作者在學書治印歷程中所表現出的“借古開今”精神,以及他為故鄉文化事業貢獻心力的拳拳之忱,深深地感動了我。
四十多年前,我在故鄉溫州的中學任教。數十年過去,有少數學生,會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張索同學就是這樣的學生。不過,那時他的名字是“張純凡”。這是一個1979屆的高中畢業班,我擔任語文老師。純凡同學的特點是特別“癡迷”于個人的興趣愛好,我記得他的興趣是畫畫,他常常出現在教師宿舍的大院中,那是來請教美術課老教師張崇棣先生的。這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我也愛好美術。多年后,他為張老師出了一本大畫冊,還曾請我為畫冊題辭。那年他考取了物理學專業,這卻是我沒有想到的。那一年,國內開始研究生招生,我也不免心動,嘗試一考,結果成了上海戲劇學院的首屆研究生。在我啟程赴滬的前夕,純凡專門來到我處,贈送我兩方圖章。這是他專門請書法家林劍丹先生為我篆刻的。這時,我才知道,純凡正在劍丹先生處學習書法。四十年來,這兩方圖章為我所珍藏,也是我使用最多的藝術印章。讀了眼前的這個文集,我又了解到,原來純凡大學剛畢業時,曾在溫州博物館做過臨時工,從那時開始向博物館老館長、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請教刀耕。而方先生卻是我祖父的友人,亦是劍丹先生的篆刻老師。純凡的好處就是善于自我設計學習目標,拜師學藝,不斷提升自己的藝術創造能力。
不知什么時候開始,純凡更名為“張索”,我在很長時間后才適應這個新名字。幾十年間,張索同學常常邀請我參加故鄉的文化活動。當時的溫州市長錢興中特別關注文化建設,張索不僅是思想敏捷的出謀劃策者,而且是盡心盡力的、不辭辛勞的實行者。熱心負責是他的天性。溫州圖書館的對聯設計、籀園的溫州教育史館、諸多文化名人的紀念活動,都曾經留下了他的創造才情和辛勤勞作。他為“世界溫州人大會”設計了會標,還約請我為“詩之島”——江心嶼寫一首歌詞,并請溫州的民間音樂家潘悟霖傾情譜曲,這一首《情系江心嶼》于當年的活動期間在故鄉傳唱。溫州大學校史博物館是張索的杰作。溫大是他的母校,他學習于斯并工作于斯。為尋求學校的歷史軌跡,他東奔西走,千方百計找到八十年間大量的照片,通過多種途徑尋找照片里師生的名字,使每個進入陳列館的校友都會找到自己的資料,還有許多校友捐贈的學校“文物”。這真是個奇跡!我是溫大前身溫州師范學校的學生,也算是半個多世紀前的校友。2013年5月,我參加母校八十周年校慶活動,參觀了大羅山下溯初亭畔的這個博物館,為之震驚。此后,我逢人便說溫大的校史館,毫無疑義,這絕對是全國之最。
不久后,他調來上海,在華東師范大學擔任書法篆刻的研究生導師。他與我一樣,都是由故鄉溫州來到了大上海,但不同的是,他會提出一種說法:“讓人走開,把心留住。”表示他非常自覺地把心留在東甌故土。
他有一篇文章寫他對“海派文化”的認識。他認為“海納百川”是海派文化發展的第一步,而“海灌百川”是海派文化基于海納百川后的發展階段。他把海派文化散射到全國各地,對原籍老家產生深遠影響的現象稱為“海灌百川”。近百年來,海派的繪畫書法中吸納了許多“永嘉畫派”的人物與藝術,并又反作用于“永嘉畫派”。這正是“納”與“灌”的表現。張索近年的文化活動來回于溫州與上海之間,很能表現出這種“納”與“灌”的關系。他于近年促使上海市文聯與華東師大創建“上海市中國書法研究中心”,正顯示了重振海派書法的雄心。
張索到華東師大不久,就策劃了一個馬公愚先生的書畫展。溫州人馬公愚早年曾任上海大夏大學的教授,而大夏大學正是華東師大的前身。在上海圖書館的大展廳中,這一場展覽向社會顯示了華東師大書法專業的淵源。溫州出身的畫家書法家長期間在上海的藝壇上大放異彩。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馬公愚、方介堪直至當代的劉旦宅、林曦明等都是代表人物。我祖父一萊先生當年在上海工作時,與馬公、方公等文化人都曾是同鄉好友。伯父子圣先生就曾拜在馬公門下學書。張索在歷史文獻中看到了這種關系,就將子圣先生亦請到展覽現場,并參加學術研討會。當時,子圣先生已年近百歲,他的發言可謂句句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在華東師大這個優良的教育平臺上,張索傾注了自己的熱忱與愛心,開拓了書法教育的一片基地,并很快地使這一個基地成了全國書法教學的中心之一。作為教師,我特別贊賞他的一些教學理念與行為。他強調提出學生要以“持敬守正”之心來傳承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他認為“敬”是中國文化傳承中的一個核心思想,中國文化就是在“持敬”的前提下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他為學生開出“金石學”“文字學”“詩詞學”等相關專業的課程,選聘名家名師任教。以此深培學生的文化底蘊,提升學生的綜合藝術素養,希望學生成為視野開闊的文化人,而不作徒有其表的寫字匠。他還要求學生堅持用毛筆寫日記,一則可以提升書寫水平,再則可以學習文言寫作,而且可以磨礪心性、鍛煉恒心,并以此而使書法學習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我始終以為,揮毫作書,應有“詩書畫”全面素養的基礎,潛心治學,則須有“文史哲”總體精神的底氣,如此方有可能致深行遠而成大器。我高興地看到,張索在為學生培養人文精神的同時,他自己亦在努力踐行,真正體現出“教學相長”的良性結果。他以自己的治學精神和藝術成就為學生樹立榜樣,亦因此而深受學生的敬佩與愛戴。
此刻,我正翻閱著張索君的文集,眼前的文字令我感動、令我深思。“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古圣賢之言在我心中輝映。我從這一篇篇藝術家的知性文字中,看到了作者的高遠寄興和豪邁襟懷,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他以“敬”待物的為人處世特點。他敬師、敬鄉、敬賢、敬業,總是以崇敬之心,行守正之事,并以崇古之誠,創開今之業。今次,他把自己的文集定名為《持敬集》,其有深意在焉。
2020年8月18日于滬西周橋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